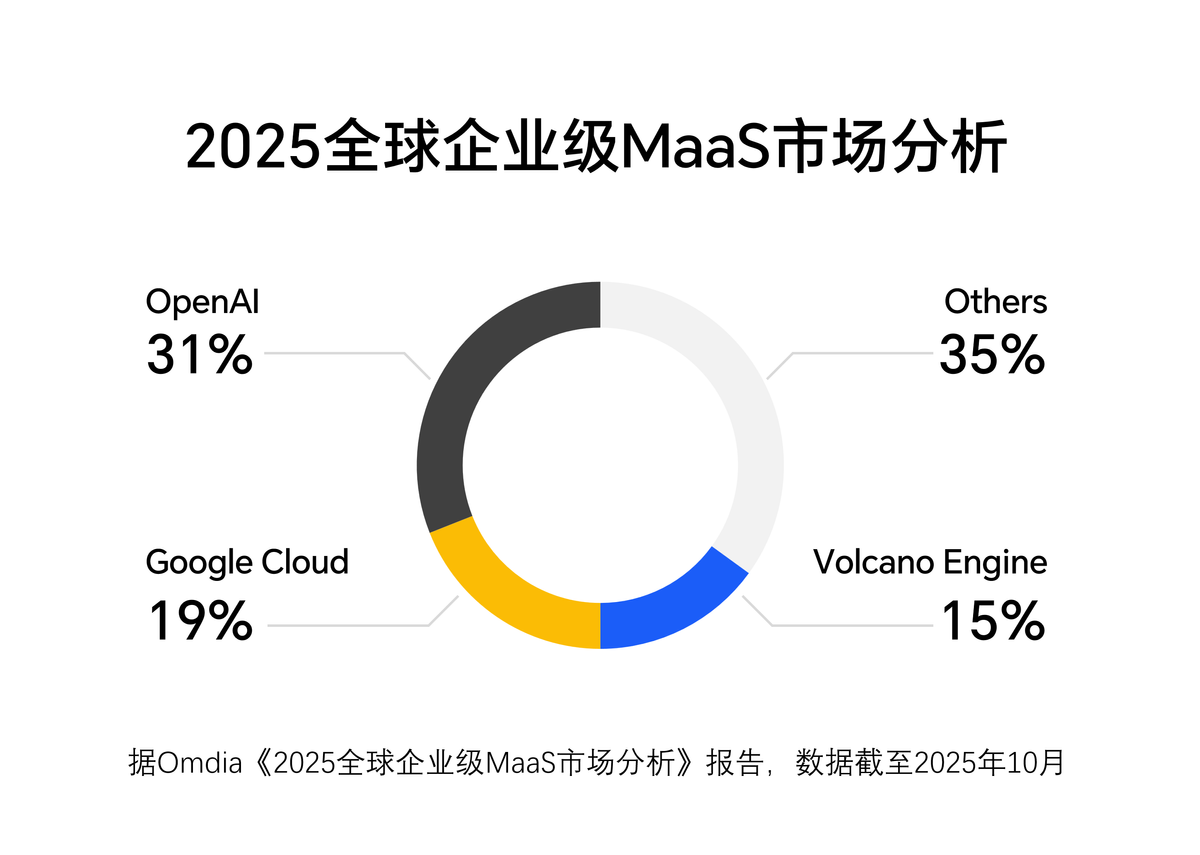不是吧!钢铁企业的员工收入能比肩BAT?|钢铁数字化云沙龙(上)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全面落实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拓展节能减排新途径,实现钢铁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此前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数字化转型已是各钢铁企业发展的战略之一。
针对这一趋势,《经济观察报》组织了2021数字化转型百强峰会创新云沙龙之“钢铁行业数字化”专场,邀请了河钢数字技术公司首席技术官贾永坡博士,荣程新智研究院执行院长、荣程智能制造总设计师金涛女士,金蝶中国钢铁行业事业部总经理陈宝生先生三位资深行业专家,对企业在数字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进行深度剖析与分享。
小编特别整理编辑沙龙精彩内容,分成上、下两篇文章与您分享。

陈 白
经济观察报商业评论主编
大家好,我们今天的对话从行业政策开始聊起,现在政策变化非常大,国家对钢铁行业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我想问一下各位所在的公司落实新政策这块的战略是怎样的?

金 涛
荣程新智研究院执行院长
荣程智能制造总设计师
我认为“十四五”期间国家对钢铁行业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三个词:第一个词是低碳节能;第二个词是智能制造;第三个词是质量效益。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词的顺序换一下。
第一个词咱们先说质量效应,因为对于制造行业来说,不管我们是推数字化还是智能化或是各种其他技术,我们最终要回归的是制造的本质,我们要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但是,质量效益一定和智能制造、低碳节能是不矛盾的,它们是并行的。因为在我过往的经验中,很多次我们都发现当质量和效率上去了,我们也节能了,环保了,做到智能化了,所以这个行业是能够做到多目标寻优的。
那第二个词是什么?是低碳节能。企业生产追求效益,控制成本是至关重要的途径,成本就反映在你是不是少用能耗了,是不是少排放二氧化碳,所以质量效益和低碳节能的目标是一致的。
第三个才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是用数字化还是用智能化的手段。
所以,我把这三个词换一下顺序,第一是质量效益,然后是低碳节能,最后才是智能制造。这是我认为的三个主题词,我稍后会对这三个主题词,做深入的解读。

贾永坡
河钢数字技术公司首席技术官
对于国家政策这一块,河钢集团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对于国家政策的理解就是“制造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河钢集团光是为实现超低排放,近几年就投入了200多个亿。我们现在有两个国家级的绿色工厂,拿了世界钢铁工业可持续发展卓越奖。基于我们生产实际形成了一些前沿的超低排放技术,比如说脱硫脱硝,比如除尘技术。因此我认为在绿色发展这块,我们钢厂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超低排放的要求。

河钢“绿色工厂”
第二个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就是使生产更加智能化。近几年来,我们把智能制造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钢铁的产线深度融合来提质降本增效。
在落实国家双碳战略这方面,国家要求2030实现碳达峰(中国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让二氧化碳排放量“收支相抵”, 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但河钢集团的目标是在2022年实现碳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我们比国家碳达峰时间提前了八年,比国家碳中和时间提前了十年。

金 涛
荣程新智研究院执行院长
荣程智能制造总设计师
刚才谈了一个非常好的话题,碳排放。其实这不仅是在钢铁行业或是整个制造行业,我觉得是所有企业都在谈论的一个话题。今年二月份,荣程和冶金规划院做了全国钢铁行业的第一个双碳规划,我们站在顶层来看,为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们要从工艺、装备、信息化等层面如何改进和变革。
在做完规划之后,我们从集团层面做了五个调整:
第一个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我们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来解决碳排放的结构,才能做到碳中和,达峰容易,但是中和挺难的。原来整个荣程体系以制造业为主,经过几年调整,制造板块在整个营收里降至30%-35%,以大宗贸易为主的第三产业上升到了60%,我们已经由一个原来只做制造业的企业向服务型制造业转型。
第二个调整是能源调整。只有用能结构调整了,才能往下实现减排。能源调整又分了几项:第一项是高炉冶炼,我们原来是用碳和煤,现在我们用氢冶金的方式,用氢气来做还原;第二个变化是在运输环节改变用能结构,我们不再用传统的柴油车了,我们改用氢气卡车,我们加大了海运的比重,还更多地使用了“公转铁”(大宗商品从公路运输转到铁路运输上来)这些都是在用能结构上做的变化;此外,我们开始加大绿电比率,今年我们自己装了很多光伏发电。这些都是我们在能源结构上的调整。

荣程氢能源车辆
第三个调整是产品调整。就是把能量用到更高端、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去,这样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就降低了。
第四个调整是用能节俭。在钢铁行业里,从原料到变成铁水这段我们叫铁区,铁区是能耗最大的部分,70%的能耗发生在这里。我们把铁区所有的数据收集起来,然后一道一道地分析每一个工序、每一个时段里物质流的变化,把物质流全部跟踪起来,相当于我们把铁区的碳足迹就给跟踪起来了。
我们跟踪碳足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来分析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这些时间点上该不该发生,应该发生多少,还有多少降低的空间,然后来优化这个结构。
我们的第五个调整是工艺的变化。比如说我们把长流程改成短流程,我们现在有一座转炉,我们开始变成电炉。通过这样的转变,我们可以使用更多的废钢,尽量少购买铁矿石。
我们通过这五个调整来实现低碳节能。
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件我认为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认为减少碳排放不只是企业的事,其实是地球上每一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做了一个APP,叫“爱森”,号召我们每一个员工去做一个低碳达人。员工可以通过低碳的通勤方式在爱森上赚取能量,能量可以用来种树,我们的员工可以用自己真真实实走出的每一步最终变成为地球的贡献一棵树。

陈 白
经济观察报商业评论主编
金院长分享了非常多好的案例,我想问问各位在钢铁行业推行这些新的技术或管理模式时,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和挑战?

贾永坡
河钢数字技术公司首席技术官
关于挑战,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是顶层设计。你要搞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它分很多的内容,有技术、管理、流程、业务等,如何在涉及到方方面的情况下做顶层设计,这是比较难的。即使有了顶层设计,往下落实的时候,你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技术和场景的结合。我们都知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这些技术在消费互联网这些行业有了非常多的突破,但是怎么和钢铁行业来进行深度的融合,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举个例子,刚才金院长提到了双碳减排要吃废钢,这就涉及到利用视觉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废钢的问题,刚好我是负责这块研发的,我们刚研发了一款废钢识别的产品。但是并不是所有场景都能像这个例子一样,能很好的把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和钢铁行业去结合。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结合,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还是点,由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第三个挑战是人才。我们有非常多懂钢铁工艺的人才,但是数字化人才非常紧缺,钢铁行业对于高端人才的吸引力远远不够。今年,我看新闻说腾讯把毕业生起薪提到了40万,校招的人数扩大了40%,美团还扩大了一倍,这让钢铁行业招引高端人才更加困难,因为优秀的计算机行业毕业生总是有限的。

陈宝生
金蝶中国钢铁行业事业部总经理
我们金蝶从2001年开始进入做钢铁行业,到现在整整20年时间。我们跟国内的许多大中型企业,包括央企、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都有合作,荣程和河钢都跟我们合作了十五六年了。我们发现企业转型面临的挑战主要有这几大方面:第一是运营,第二个是管理转型,第三是组织架构转型,第四是思想转型。
转型其实就是转心,你要有决心、耐心和恒心。转型不是老板的事情,也不是信息化总监和IT人员的事情,是每一位员工的事情。
还有,像贾博士刚才讲的这个问题,现在学计算机的人员是挺多,但是进BAT的多,到传统制造型企业的少,孩子们和家长普遍对传统的制造企业不认可,认为我们钢铁行业还是传统的“老大黑粗”,实际上他们现在真的应该走进我们钢铁企业去看看,现在好多钢铁企业真的是花园式的,非常漂亮。

河钢集团钢铁厂区

荣程集团钢铁厂区
其实各个企业碰到的问题,金蝶也会碰到,因为我们一直在不断转型,大家知道我们集团的徐主席爱“砸东西”,实际上就是不破不立,要把一些旧的东西砸掉,创建新的东西。为了转型,我们把我们在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些产品线砍掉,我们要转云,要上云。

金蝶转型之路
所以转型就是要从心上去转。如果心上不转,不坚定,只是看着别人怎么做,我们也要去做,那就是为别人做的,没用的。

金 涛
荣程新智研究院执行院长
荣程智能制造总设计师
我补充说一下,我认为刚才宝生说的“转型就是转心”,真的是非常对,我们也感受到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上的难度,而是心和脑的问题。我分享一个案例,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搞了个面向智能制造的“灯塔工厂”评选。
“灯塔工厂”的评选不是听企业自己说做了什么,而是所有的调查人员进驻到你的企业里去听你的员工说他们怎么看智能制造,怎么看数字化。只有当每一个员工的心变了,他开始觉得自己是智能制造的一份子、是数字化的一份子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企业转型。
我们再来说一下人才结构。当我们说到数字化的时候,大家都会认为数字化就是那些学计算机的人,其实不是。数字化涉及的专业是非常多的,涉及到最底层的设备、仪器仪表、自动化,然后再往上才是信息化,再往上还有很多。整个钢铁行业里数字化相关的专业有二十七八个。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呼吁一下,我们在看数字化的时候,不要只盯着信息化,信息化的人才我们缺,但是我们也缺很多其他专业人才。

陈 白
经济观察报商业评论主编
各位都谈到钢铁行业的人才结构的问题,现在国家也在推职高,包括职业教育。我想知道大家觉得合理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人才结构是怎样的?

贾永坡
河钢数字技术公司首席技术官
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愿意去制造业??我认为跟收入有很大关系,不同行业收入的差别,导致年轻人不愿意去收入相对更低的传统行业。
从国家层面看,我认为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高端、高收入的岗位是供给不足。为什么现在是计算机行业、互联网行业,很多人能拿到高薪,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里能在全世界分得一杯羹,因此我们能在这个行业里拿到高端的供给配额,而其他行业的高端岗位供给不足。举个例子,为什么机械行业在德国就可以拿到一个不比计算机行业差太多的薪水,还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不足,所以高端供给的岗位没有在我们国家。如果我们国家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把国外的这些高端供给岗位抢到中国市场,我想机械行业也会成为一个非常吃香的行业。
就拿芯片行业来讲,我们设计的薪水都很高,但是在制造环节还跟海外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技术方面,我们还要去买国外的光刻机,即使我们花十亿去买,人家也不一定卖给我们。这个行业的高端供给目前在荷兰,不在中国。
因此,如果我们有决心、带着很高的期望去促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无论你来自普通高中还是职高,无论你是白领、金领还是蓝领,都能拥有非常体面的收入和生活。
计算机行业进腾讯的毕业生起薪可以到40万,可是我们全中国有多少人年薪能够到10万?总理之前说我国有六亿人月薪不到1000,这是一个巨大的鸿沟,背后是结构性的差别。我个人认为是我们没有这么多高收入的岗位,假设我们有几千万到一个亿的高收入岗位,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发展水平会远远高于现在。因为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一个基础性的行业,没有制造业这个国家说话都是不硬气的。
很多“脱实向虚”的国家,遇到疫情他们的整个供应链就断了,他们没有能力去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只有我们中国才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支撑得起内循环,可以支撑得起清零的这项政策,去保证生命至上的最高追求。

金 涛
荣程新智研究院执行院长
荣程智能制造总设计师
我认为,智能制造是在用更好的先进技术去辅助人,朝着人机协同的方向去发展,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将来的工厂智慧到什么程度,它终究是有人的存在的。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认为将来制造业的从业者,其实还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每一个层级发挥相应的作用,刚才咱们贾博士说的这种高端岗位的供给,往塔尖上走的这些人,他要做到能够引领方向。我也想招这种塔尖的人,所以我们不是在和制造业抢人才,我们确实是在和互联网抢人才。抢什么人?抢算法的人,抢开发的人。
以我个人情况来说,我当初之所以投身制造业是因为我认为再往后看几十年,中国还是要以制造业为基础,制造业能让我能学到更多的东西,我也能做更多的事,所以这个里面有我个人的情怀,我相信现在的大学生里,会有和我一样有投身制造业情怀的人。
其实制造业的环境已经和我们原来电视里看到的烟囱林立、黑烟浓浓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刚完工的一个铁区集控中心,我们是按照艺术标准来建设的,很多人参观完以后会觉得这是一个博物馆、艺术馆,不会觉得这个是我们工人操作的车间,这是制造业和大家想象中不一样的一面,还有一面是制造业目前并不是大家经常在一些纪录片里看到的全自动无人化,我们是人机协同。尤其是在流程行业,人机协同一定是我们会持续去做的,而不是把所有工厂都给做成“关灯工厂”、“黑灯工厂”。


陈宝生
金蝶中国钢铁行业事业部总经理
关于行业收入,其实我们工厂审计部的一个经理、一个钢铁企业的IT总监都能够年薪千万,可是这样的报道很少。所以,我建议首先在宣传层面,类似像我们经济观察报等这些媒体能够多走进、多宣传我们制造型企业;第二是学校的课程要加强实用性,现在我们能看到大学的课程会设计走进企业的内容,让学生真正参加实践,我们国家的教育已经在调整了。
在我们制造型企业里,我们需要的人才结构,是不断优化的,我们需要的高端人才不只是IT人员。在我们很多做得好的项目上,优秀的的财务人员会具备IT的思维,他要搞个什么东西,会先想到如何去立项,用项目的方式来管理。
我们原来是农业大国,现在我们已经是钢铁大国,但是从钢铁大国到钢铁强国,我们还需要时间。我相信,通过人才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再加上我们舆论宣传调整,人的观念也会慢慢调整,我们会向真正的强国迈进。
----------------------
(市场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据此投资交易,风险自担。)